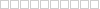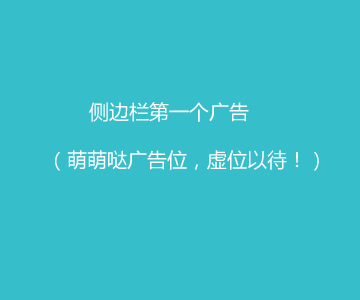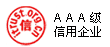小度有多少故事(小度的故事有哪些)
【温馨提示】本文共有8758个字,预计阅读完需要22分钟,请仔细阅读哦!
《县委大院》有多接地气?追剧的同时仿佛在加班!,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光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国剧经典制作班底,一众戏骨演员入戏。12月16日,“热菜”上桌,浙江卫视年度压轴大剧《县委大院》定档播出。 作为一部以县级基层治理为全景展开的电视剧,观众跟随代县长梅晓歌(胡歌 饰)推开县委大院的这扇门,看到的是万千基层景象。《县委大院》以大处着眼的选题突破、小处着手的创作之诚,既展现出基层治理“按下葫芦起来瓢”的琐碎平凡,也有县城生活的市井烟火,将基层治理的议题包裹在平常的生活中。 自开播以来,浙江卫视《县委大院》短视频新媒体矩阵播放总量破4000万,单条点赞破8万,单条视频播放量高达1000万。人物和故事出彩、有嚼头,《县委大院》接住了观众的高期待。 01 真实度拉满 白描基层现实生活 @笑逗菌:作为主旋律剧,尤其还是这种基层剧,自然需要真实的质感。真实是无浓厚的磨皮滤镜,基本上都是最为真实自然的人物状态,以及场景打造。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脸上清晰可见的纹理粗糙感。 @小埋碎碎念:等人做准备的时候的忐忑心理,有注意各种细节的领导心细如发,形式上给弄的很好。还会有一些各种意外,还有拖后腿的同事。好的地方越来越好,不好的地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整个的真实住了! @卖安利的青岛贵妇:猪肝色的桌子、红色座机、蓝色的文件夹以及打印机等等,每一个道具都准备的相当充分,剧中的每一个小细节都拿捏的十分到位,真正只有用心制作才能获得成功。 @追星阿姨李纳尼:一些我看了之后拍手叫好的细节有!黄磊老师饰演的吕青山和拆迁钉子户谈话时墙头围观的村民们真的很现实了,把现实生活中民众好事围观的场面精准还原!不仅如此还有村长这个大嗓门真的一比一还原的我们村长的说话音量!有被这些细节可爱到~ 02 人间烟火气 群像鲜活不刻板 @土包姥姥:《县委大院》是一部群像剧,整个剧情是虽说围绕着胡歌饰演的光明县县长(县委书记)梅晓歌,但该剧出场了很多配角,使整部剧看起来更加丰满。《县委大院》男性角色的戏份偏多,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女性角色如艾鲜枝镜头越来越多,成了剧中一道亮丽风景。 @光明县村口二大爷:观众只要进入剧集营造的场域,就能慢慢了解剧中那些基层干部的脾性与追求,他们的形象很自然地浮现在观众心间,从而实现“于平淡中见不凡,于简约中见博大”的艺术效果。 @在水一芳3210153812:《县委大院》首部描写基层工作人员群像作品,打破以往固有的脸谱化,程式化性格和形象,主角配角角色特征鲜明,基层各种人物具有代表性,有温和派,强势派多种工作作风。 @巨巨想萌萌哒:最近的精神动力,来自县委大院的艾鲜枝,基层鲜活的女领导。为啥要有女领导,在遇到某些问题时,她们就是能更感同身受! 03 一人可千面 剧抛式演技引共振 @胡椒粉味紫米饭:之前还想,依照胡歌的气质,可能不太适合演这种朴实接地气儿的角色,结果,看了头两集,就立马让我改变想法了,这活脱脱就是县委干部嘛。你胡真的是神奇的存在,感觉他是能把自己变成任何一个他所饰演的角色,这些角色还都不相同。 @酸梅很甜h:胡歌的演绎落在实地上,人物沉稳,不摆架子,眼神始终坚定无比,新官上任时的状态自然真实,动作形态都和角色非常贴合,等到了深入群众的时候,梅晓歌的亲和力让人放下戒备,对于拆迁户的抗拒有着无尽的包容,毫无疑问,这个亲切、能干的书记被演活了。 @追剧:《县委大院》艾书记是真的有点子行动力在身上的,这沟通力,决断力真的很厉害,而且能看出来,艾鲜枝真的把沟通之术拿捏了,能发现的了问题,也能先礼后兵的拿捏钉子户,好喜欢吴越这剧抛式演技! @被窝是咩咩羊:梅晓歌,一个浪漫的、理想化的改革者,做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他不是一个符号化的形象,他是一个有生活、有目标、有情感的鲜活的人。而胡歌把梅晓歌完美的演绎了出来。 大院内的日常工作,大院外的平凡生活,《县委大院》生活流叙事独有的烟火气与亲切感,拉近了剧集与观众的距离。每天19:30,锁定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与《县委大院》一起守护烟火人间。 文章来源 /广电时评 来源: 浙江卫视中国蓝 ◎唐山 “我的灵魂某些碎片被留在受创现场,我一直困在那里,我的人生卡住了,哪里也去不了”“我很害怕自己坏掉,还是其实我已经坏掉了,你觉得我会好吗”……面对《她和她的她》中这些台词,抑制泪水便成了一件困难的事。 只看前三集,《她和她的她》堪称催人弃剧:女主角(许玮甯饰)因车祸失忆,被意外牵扯到杀人案中,警察追凶,女主修复记忆,警察与女主暧昧……三线穿插,全是俗得不能再俗的梗。为故事而故事,为悬疑而悬疑,在今天,会有多少人被它套路呢? 然而,从第六集开始,《她和她的她》突然逆转,这时才发现,它并不想讲一个热闹的悬疑故事,而是直面社会、批判现实,只是太温柔、太曲折,对于习惯匕首与投枪的人们来说,不易体察。 《她和她的她》的主题近似《德伯家的苔丝》,呈现出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女性的苦难、恐惧和被扭曲——剧中女主高三时被辅导老师性侵,这成了她的一生之痛,她努力装成“二男人”,高冷、强势、职业、傲慢,可无论怎样成功、怎样忘却,她始终无法摆脱过去,甚至因此丧失了爱的能力……可如何把这样的“老话题”,讲出新花样,既有本土特色,又能深入人心呢? 《她和她的她》是一个样板。 在故事中嵌入“想象的故事” 《她和她的她》中采用了“对位”的叙事方法,即用不同逻辑讲述同一故事。 故事一:女主是猎头业的“十大金牌经理人”,被迫做老板亲戚、新入职的杜骏儒副手。因工作繁忙,女主与家乡的母亲往来甚少,与男友亦有感情裂痕,在男友准备求婚的当天,女主与他正式分手。女主与杜骏儒的合作冲突不断,杜骏儒竟试图性侵女主。女主在逃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 支撑这段故事的逻辑是虚假的:表面看,职场与生活的冲突是女主面临的主要困境,为了事业,她不得不放弃爱、亲情,但真正原因并非如此。 故事二:女主从车祸中醒来,已完全失忆,父母和弟弟处处呵护着她。女主当年的补习班老师在疗养院被杀,警方怀疑女主的好友、失踪的颜圣华是凶手,颜圣华当年和女主一起上补习班,后在疗养院当护士。为找到颜圣华,警方与女主密切接触。让女主惊讶的是,负责该案的警察竟是她刚分手的男朋友。 男朋友何时当警察了?这其实是该剧刻意留下的一个线索:追寻记忆和破案过程,都是女主在车祸后脑补出来的,半真半假。 首先,女主的男朋友不是警察。其二,补习班老师没被杀,而是自然死亡。其三,女主的父亲、弟弟早已离世。 想象出破案过程,让女主渐渐想起,高三时,她和颜圣华均曾遭补习班老师性侵。女主当时想报案,却意外退缩了。大学时,女主谈过一个男友,并向对方坦白了曾经的经历,前男友选择离开,这对女主构成了二次伤害。她害怕和后来的男友谈论过去,她努力忘掉原生家庭,只有成功,才能遮掩她内心的孤独。 故事三:女主重回职场时,杜骏儒竟谎称女主纠缠他,向老板告状,导致女主被开除。经历内心反复折磨,女主决定诉诸法律,而杜骏儒的妻子恰好是颜圣华,她试图忘记过去,不愿帮助女主,但在冰冷的现实之下,她还是把证据偷了出来,交给女主。 将“心理现实”巧妙嵌入现实 显然,三个故事是一个大的线性故事,《她和她的她》将主干(即故事二)换成“心理现实”,立刻峰回路转。比如: 把男友变成警察“小刘”,并非写实,但表达了女主的内心渴望。她需要一份心灵上的安全感,不仅仅是甜言蜜语,而是让她能不再恐惧,这恐惧一直追赶着她。在想象中,女主给男友添上一点“痞”气,这是她所能想象的、最后的英雄气概,足以包容一切。 把补习班老师的死想象成一场命案,说明女主试图“杀死过去”。女主的理性又推导出,父亲、弟弟,乃至受害者颜圣华,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女主与弟弟的关系又特别亲昵,所以在剧中,她反复追忆二人成长过程中的美好片段。 想象只是一种疗伤策略,它无法撼动现实的残酷。在女主的“心理现实”中,“关键时刻”仍在,包括—— 女主意识到老师的非分之想,试图不再去补习班时,却遭父母呵斥。父母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将女主的逃避视为偷懒、不负责。在最需要父母呵护时,恐惧让女主不敢说出真实想法,导致受害。 女主被性侵后,为缓解内心的恐慌,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闺蜜,结果被迅速传开,女主对人的信任从此崩溃。闺蜜们从没想过,她们养育出的偷窥文化还会反噬。女主的闺蜜成年后,同意男友拍私密视频,对方转手便将其贴到网上,她被暴露在公众的视野…… “对位”的手法拓展了《她和她的她》的讲述空间,使它从一个单向度的悬疑故事,变成复杂故事,从而有了写人的空间——同样的人物,通过不同方式讲述,不断发生变化,这种错位感逼人反省:在女主“工作狂”的面具下,竟有一个如此痛苦的灵魂,那么,我的面具是什么?它是不是也在遮蔽着我的生命之痛? 女性突围之难 有了写人空间,就要把人真正写好,这是《她和她的她》的胜场,剧中勾勒出现代女性的群像,隐喻女性从现实突围之难。 剧中女主性格坚强、自立,似是所谓的“新女性”,但她动辄把工作情绪带到生活中,她有梦想,却不知如何表达,只能在加密的私人博客中自怨自艾。在那里,她坦承自己怎么也走不出被性侵的经历,她为此付出的努力,乃至她的精神痛苦……性侵给女性带来的伤害可能终生相伴,它通过篡改女性的自我意识,不断扩大其伤害。如果不是男友看了女主的加密博客,他也无法真正理解。 补习班老师的夫人则是一个奇怪的角色,她明知丈夫的恶行,却把怨恨转嫁到颜圣华、女主头上,通过将受害者贴上“有罪”标签,她坦然成了帮凶,她唯一的不满,是老公中风后,她不得不长期照顾他,太“吃亏了”。 类似的女性并非个案,在职场上,方主任天天惦记“小鲜肉”男同事给她按摩,以证明自己还有魅力。她要求女下属必须化妆上岗,不能太浓,也不能太淡。为多抢业务,公司鼓励女员工和男客户陪酒,她却觉得理所当然。 方主任和补习班老师的夫人代表着一股浊流,她们身为女性,却主动泯灭了女性意识,他们更愿屈从于男性视角来评判一切。 《她和她的她》中的女性们在挣扎中遭遇的往往是来自同性的嫉妒、干扰、牵扯和伤害,恰恰表明女性单独突围之难。正如萧红所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她们真正要突破的,是一道由偏见、不公、恶传统、虚伪、自私等构成的厚墙。 真正的女性视角 近年来,试图表达女性声音的作品不罕见,甚至一度无“大女主”不成剧,可真正传达出性别平等内涵的却不多。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创作者们多从男性视角解读性别平等,将其视为一场斗争,套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公式,似乎女性在体力上打败男性,在智谋上算计男性,在权利上压倒男性,即为性别平等。 这就带来两大误会:部分男性觉得女性权利已高于男性,觉得不公平;中国的性别平等状况较好,不必再进一步。 误会的产生,源于不了解女性真实感受,以为女性的恐惧、示弱、避让是“与生俱来”的,而非社会结果。如果不倾听,如果不反省,女性的困境就似乎不存在。《她和她的她》的价值在于,它脱离了非黑即白、你多了我就少了的男性思维框架。 “大女主”传承的依然是男性文化,依然是对权力、金钱、地位的疯狂追逐。通过黑白分明的截然对立,创造出貌似壮怀激烈回肠荡气的效果,但它们的背后是惊人的无聊与干瘪。 《她和她的她》中内涵着传统的审美原则,即斯文。它不是“钢珠落在钢板上”,而是“乐而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它体现了克制陈述、娓娓道来的风度,这更接近女性体验——它是日常的、具身的、平和的、反崇高的,它有自己的美好与意味。在剧中,女主连绵的倾诉、追问、哀叹、自我检讨中,并没指向共通的解决方案,甚至没有批判谁、怨恨谁,而是用唤醒同情的方式说服——人生注定含辛茹苦,为何不能彼此扶持? 斯文是有力量的,它是前贤的精神家园,也是传统所在。即使我们这一代人还不太能读懂它,我们的下一代人注定会被它陶醉。不应否认斗争的声音,但更应珍重斯文的声音。《她和她的她》之妙,恰好就在于它传达出久违的、斯文的声音。 在北京地铁1号线五棵松站轨道下3.67米的深处,一根内径约4米的巨大输水管道穿行而过。每天清晨出门前,人们拧开水龙头流出的每一滴水中,有70%都来自汉江。这条长江第一大支流跋涉1260公里而来,哺育着北方6000多万人口。 多年后,身居北京的袁凌偶然得知,原来自己又一次喝上了汉江水。在他出生的陕西安康,汉水穿城而过,那曾是他年少时泅渡冒险的处所。他亦记得初见汉水时的震撼,那宽度从未见过,“人不过是晾晒在大堤上的一片衣物”。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开始通水,到今年是第八年。在水龙头流出的细流之前,有许多故事连同这根输水管道,一并埋在了3.67米的深处。 一段尚在自由流淌的汉江,云山苍茫,江水迅疾。不久将成为平静的库区。(拍摄:袁凌) 从《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到《寂静的孩子》,在非虚构概念尚未流行时,袁凌就已经开始相关的创作。他关注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曲折故事,只是记录,不做解释,将人还原为“人”。这本《汉水的身世》也许并非是他笔下关注度最高的故事,却是他所奉行的这套准则一以贯之下的坚持。八年间,他陆续走访了汉江沿线的移民、纤夫、船工、渔夫和沿岸老街的居民,在物是人非的叙述中描摹个体的命运如何在时代的洪流间摆荡。 这些年,国内的非虚构写作也越发热闹,我们不时能看到许多直抵人心的故事,这些曾经是袁凌那一代特稿作者所希望看到的趋势——发现宏大叙事之外的“普通人”。但在喷涌的流量与关注背后,袁凌也在思考,围绕个体展开的叙事就是个体叙事吗?非虚构写作何时才能走出靠“题材”出圈的僵局?当个体的遭遇裹挟着时代的焦虑,我们还能够接受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吗,无关社会学式的解剖与分析,只是将视线拉回个体的感受与诉说。 借新书出版的机会,我们采访了袁凌,从汉水八年走访的见闻聊起,延伸至他对当下非虚构写作的观察。在不确定性笼罩的今天,袁凌多次提到,“我也都接受了”,但在接受之外,他其实依然保留了一些最初的坚持,而这也许是他在面对不确定时依稀握着的那份确定感的来源之一。 采访快结束时,我正在收拾东西,抬头发现袁凌的眼神一直停留在桌上的那本样书上。也许是注意到我在看他,他小声问:“我能看一眼这本书吗?”我惊讶,连忙说当然可以,心想这原本也是“你的书”。他拿过书开始一页一页翻,苦笑着说,“自打写完,我都还没看到过纸质版”,一边调侃,没想到现在连样书的纸质都这么好。算算日子,本来今天就应该能拿到书了,“可能是物流耽搁了吧”,他安慰自己。 袁凌感慨,这两年自己的运气一直不好。去年一年几乎没出来什么东西,今年《记忆之城》出版时,正好赶上了上海疫情严重的那几个月,订单都发不了货。那本他经营了快20年的小说,到现在为止,豆瓣上只有40多个评分。人家觉得他是个写非虚构的,也拿不准他的虚构有多少分量,只能尽量把书往大家熟悉的“人”上靠,说这是本“自传体小说”。说到这,袁凌有些情绪激动,“这根本就不是我想表达的意思”。 和以往更多在非虚构平台上发作品不同,这两年他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你很少会在非虚构的平台上看到他的名字了,但如果有翻文学杂志的习惯,也许你们会在某一篇的署名角落偶遇。 《汉水的身世》,袁凌 著,中信·大方出版社,2022年10月。 这本“汉水的身世”是他时隔三年再度带着非虚构作品,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希望它的身世能好一些吧。”说话间,袁凌叹了口气。 翻到书中的图片,袁凌忍不住指着说,你看这张,他其实是个哑巴不会说话,那天蹲在悬崖边上的那一幕,当时我就觉得整个世界都突然安静了。还有这张,黑白照片看不出来这个水的颜色,我给你看我手机里的原图,水质真的很糟糕,你都无法想象怎么会是那种颜色。还有这里,当时我在路边闲逛,路过一个地摊,随手翻开了那本书,看到水泡过后在书页上留下的那道水渍时,一下子就觉得像是回到当年那个时刻。你看,这个就是“水娃子”,这就是我们说起的那个太公,后来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袁凌不时询问:“开头那几个问题我都表达清楚了吗?刚开始时还有些拘谨,有没有我没说明白的?” 我回答说,清楚了,都很清楚。 袁凌,生于陕西平利,《新京报》2017年度致敬作家,腾讯书院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等;出版作品《汉水的身世》《记忆之城》《生死课》《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会消失》《世界》《寂静的孩子》等。 用八年时间,写一条河的过往 新京报:不同于你此前的作品,《汉水的身世》不再是由一个个单篇构成的故事集,其中出现了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汉江。最初是什么让你萌生了想要写一条河的想法?从2014年算起,到今年成书,前后经历了大概8年时间,为什么会持续了这么久? 袁凌:这个想法由来已久,我本身就是在汉水流域长大,其实一直都想为她写点什么。之前我有一篇长散文《洪水》,写的就是汉江,但当时只是一个小的随笔。后来,汉江又承担了南水北调的任务,这使她与中国和我个人的关系都更加重要起来,譬如说我虽然现在远离家乡身居北京,却和北方的6000万人一样在饮用汉江调来的水。大约在2014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南水北调中线输水工程马上要通水,汉水将要被输往北方,我赶在通水前去做了个采访。那篇长报道叫作《汉水的祈祷》,两万多字。 这两年我又远在北京喝到了母亲河汉江的水,这更让我觉得需要为它写这么一本书,回馈她的恩情。这么一条伟大深远的河流,涉及这么多方面的内容,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去采访、理解和体会它,没有办法在短暂的时间内去了解一条河,即使是自己的母亲河。另外那几年,我的一部分精力在做《寂静的孩子》,穿插性地做汉水沿线的采访。由于没有长线的完整时间,采访是分主题和地域性的,比如这次去主要就围绕“移民”,下一段再去采环保有关的人,下一次再调查鱼类,当然也会有交叉;这一次去汉江下游,下一次去上游。 2020年新冠肺炎最严重的时候,湖北一带完全过不去,稍微放松后我又去采访。最后一次采访是在今年的2月,回访几个移民村,才最终完成。即便如此,八年时间,可能也还不够。 白河县卡子镇,被关闭的硫磺矿废水污染的河道。(拍摄:袁凌) 新京报:这部作品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你以写人的视角洞察了一条河的过往。千百年来,汉水以弱者的姿态维系了自身清白的质地,但其中的吊诡也在于,正是因为它的“清白”,而成了南水北调最优质的水源地。这其中透着对老庄哲学“无用之用”的省思,无用之用为大用吗?似乎也不尽然。且你在书中提到,如果说黄河流域传承的是儒家文明,那汉水沿岸就是道家的世界。从汉水的身世中,你怎么看其中的道家内涵? 袁凌:道家思想非常复杂,在汉代它曾经一度具有很高的地位,当时汉水其实地位也很高,与黄河并称,也处于中央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带,承担着长安、洛阳两京的漕运。而在以后的历史中,随着王朝东移,汉水逐渐边缘化,当它没有途径用世时,就会表现出归隐自守的一面,不像黄河那样屡次泛滥,不甘寂寞,也不像长江的地位逐次上升,由边缘而中心。 从这个角度而言,汉水确实相比于黄河、长江,有一种道家的气质在。且这一带的确道教兴盛,既是五斗米教兴起所在,也流经道教圣地武当山,我也在想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带,这可能与它离中原的核心区比较远有关吧。 与其说汉水有一种“无用之用”的退隐感,倒不如说它其实是一种“无道则隐,有道则现”的士人风骨。你看孟浩然,他在古代又被称为“癯者”,“癯”本身有退隐的意思。但这种退隐,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关怀,只不过因为屡试不被重用而已。如果说真有一个人能代表汉江的意蕴,那我想这个人就是孟浩然吧,他既想做一番事业,但实在不能实现时,也不会留恋,接受躬耕,保有一份清白。他和李白、杜甫都不是完全一样。 汉江上的采沙船。(拍摄:袁凌) 新京报:我粗略数了下,书中提到的有名有姓的多达70余人,称得上是一幅群像。相比于你此前所熟悉的单个人的短篇讲述,群像故事的呈现上会有哪些不同的考量? 袁凌:我以前写故事集比较多,一直也想寻求一个突破,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契机。另外,汉水也确实不能那么写,它是一个整体的命运。不仅其中涉及很多人的故事,还有一些甚至是“非人”的,比如环保问题,“争水”问题,都没办法用短篇的形式去呈现,我确实困惑了很久要怎么去写。 具体写作时,我发现很难按顺序去写,就尝试先从故事性最强,也是我最有把握的部分先写,也就是“黄金水道的反光”。那部分写完后我才有了些信心,然后再掉过头来写移民,这部分的材料很扎实,而这两部分也是整本书的主体,实际上到最后才写了现在成书中的首尾这两部分。 新京报:在整个走访写作过程中,有让你觉得遗憾的地方吗? 袁凌:有一次,我去一个渔民小区采访,当时正听一个渔民讲他的经历,没想到一下子拥过来十几个人。我当时压力非常大,我也没有什么“身份”,很担心会有人冲出来把我的笔和本收走。人群一下子很嘈杂,你判断不了大家各自是什么“目的”,有人在讲自己的遭遇,还有一些人则在大声问“这个人是谁”,我当时极度紧张就走了。其实人群中有一个姑娘打小生活在船上,她起初讲了些自己的故事,很动人,但确实很遗憾(我)没听下去。后来我虽然几经辗转也联系到了她的父亲,但肯定没有当时她的讲述那么生动。类似的遗憾想想也还有不少。 黄金峡江边小路上,最后一位在世的“太公”楚建忠踽踽远去的背影。(拍摄:袁凌) 新京报:书中出现了许多的“最后一位”,从最后一位在世太公楚建忠,到最后一位渔人老杨,再到汉水的最后一条大鱼,连同最后一次鱼的记忆。这些读来都有种沉重感,你似乎放下了此前写作习惯中的克制,在这本书中不再吝啬流露自己的情感? 袁凌:确实,不过这里有一部分是题材的原因,像以前那些短篇,每个故事中主人公都有他(她)人生的轨迹,你加上自己的视角是不太合适的,我能做的只是记录,帮他们把那段经历讲出来。但对于整体的写作,有些东西无法不言自明,需要一些你的判断和视角,把一些东西传达出来,它甚至可能并不拥有完整的故事,只是一个场景。 另外,写“河”本身就容易想要动起来,你会希望它有那种奔腾澎湃的气势,你不自觉就会想要写出它的那种生命力。而且坦白讲,写的时候常常会很憋屈,就不自觉地会转换成笔尖的感情吧。你眼睁睁看到一条大江被分割成蜈蚣一样,它原本可是一条流动的江哎!它现在就像蜈蚣一样分出了无数条线路,它不再是一条河往下流了,是四边形,甚至说在和长江的关系上,已经失去了河流的伦理。 新京报:所以最开始的那篇文章,(它)被叫作“祈祷”。 袁凌:过往的已经无法改变,但至少留下一个姿势。 《晚钟》,米勒绘,56cm x 66cm,布面油画,1857-1859年,现藏于巴黎奥赛美术馆。 哪怕安顿和归乡,其实也是种资源 新京报:这本书也是你自《寂静的孩子》出版,三年后再度带着非虚构作品回归公众的视野。我们也借此机会,聊聊你的近况吧。这三年间,除了准备新书,你还在做什么? 袁凌:其实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准备手头的这几本书。但同时,我也面临着很多不得不做的选择。一直到去年5月份之前,我其实都在西安。那时主要是想完成《寂静的孩子》收尾,同时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汉水的身世》上,另外,我也一直在修改年初的那本小说《记忆之城》,实际上那本书我断断续续写了快20年。我一直想两条腿走路,光写虚构,容易走向套路;而只写非虚构,又可能会慢慢忘记文学的本质,变成一种社会学式的写作。虽然这样的确比较麻烦,但我还是愿意这么去做。 又回到北京之后,你也不能光坐着写,也需要做些采访。我其实还在酝酿一个关于抑郁症的题材,下了很多的功夫,采了五六十个抑郁症患者和医生,但是一直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写。现在很多非虚构也开始有那种系列访谈式的写作,但我觉得那种呈现多少还是有些单薄……总体上,这几年我的生活轨迹大体就是采访和写作交叉,同时也写写小说吧。 新京报:你在很多次采访中都谈过对非虚构的看法,但很少听你说起,你读虚构作品的感受。 袁凌:中国的有些小说已经有点“自成一派”了。搞得很华美,但故事情节是不是成立的都很难说,一味地“无巧不成书”,“笼子金碧辉煌,但是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鸟”。环境和现实感,人文关怀,人物性格的塑造,这些文学传统中的东西在今天似乎已经被很多人丢弃了,很多人看小说都已经不会看了。我为什么一直在尝试跨文体写作,就是希望我的小说能够获得一些非虚构的质感,它的现场和细节是经得起推敲的,是可靠的、地道的叙述,它当然可以有虚构的东西,但是至少细节上是有表现力的。 《记忆之城》,袁凌 著,花城出版社,2022年3月。 新京报:其实我有些好奇的是,这个年龄做出回到西安的决定,听起来多少像是打算为后半生寻找一个安顿,为什么后来又选择回到了北京? 袁凌: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也想做一些积累,寻求一个妥协和平衡,但是现实没办法啊,它不由你的。我老婆辞职后想做媒体,西安那边没有合适的机会,后来又只好回北京。所以说我也慢慢看穿了,我曾经一直是一个很眷恋故土的人,但尤其是这两年,和故土的关联越来越少,我也慢慢习惯了背井离乡,不再寻求安顿,飘到哪里是哪里,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说实在的,虚岁已经50岁了,我也想通了,我不需要占有过多的资源,哪怕是安顿和归乡,它其实也是一种资源,如果占有不了,也不强求了。 新京报:这种转变是近两年才发生的吗? 袁凌:对,归乡一度是我前半生的执念。我记得很多年前做一次分享,有读者问我为什么总是在写乡土,我当时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我感觉没有把那笔账还完。自从《世界》出来后,我觉得我还清了,用了很大的心力写它,但这事说到底,其实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苦笑),我觉得我可能也不欠(故土)什么了吧。再就是现实中,我的确也没有能耐把自己安顿下来,慢慢就接受这个事实了。后来,我发现我也越来越偏向于写边缘人。 黄金峡上游,渔民老杨在汉江上划着他的小船。腿脚有残疾的他,只有在船上才觉得自在。 新京报:说起“边缘人”,其实在之前为数不多的一次坦露中,你提到作为采访者,会不断路过任何一种生活,看上去总在延伸着生活的经验,但实际上自己的生活却是空心的,“甚至比不上一个从事实际职业的普通人”,这是另一种“边缘”吗? 袁凌:我一度还想过做警察,送快递之类的,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经验,而不是总是在观察别人的生活。前几年,我甚至还想过参加司法考试,连书都买了,但也没结果。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可能就是这么个“边缘人”,去不停路过很多人的生活,这可能就是写作者的宿命吧。曾经这是个困扰,但这两年,我也接受了。 新京报:我注意到,去年杨潇的《重走》出版,记录了自己曾在41天中寻访西南联大的历程,而今年的这本《汉水的身世》,也可以看作是你沿汉水的溯源。非虚构写作者到了一定的阶段,都需要一段“出走”? 袁凌:写作者初期大多依托于某个平台,以单篇的文章为主,但慢慢地就会不太满足,觉得需要一种“项目式的写作”,也就是长篇非虚构。比如杨潇去写《重走》,通过一段行走,写西南联大这个“项目”。我从《寂静的孩子》开始,也是在做一种项目式的尝试。这对于自觉的写作者而言,几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砖块垒得多了,总有一天会想能不能搭个房子。但实际上,完成这个的写作者其实并不多。 《重走》,杨潇著,单读/铸刻文化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 坦白说,这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但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一方面,平台能够提供一些保障,这会很大程度上减缓压力,但这也同时意味着平台对你是有要求的,需要在一定的时限内完成一定的工作量,这中间就存在一个矛盾,看你更看重什么。另外,自己采访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有时候可以说是风险,你没有“身份”了,这也是需要克服的很大的心理障碍。再有,写大部头需要多方面的储备,如果一直在平台,可能有一些文字天赋,再加上一些勤奋就够了,但大部头就需要你有些过人之处。 新京报:项目式的写作,也意味着需要去承担一段时间内出不来“作品”的压力吧? 袁凌:其实,哪怕是有“作品”出来,也还是会有压力。从一本书开始走审校流程起,它的出版时间就已经不再是可预期的了,再加上这本书与读者见面后的那些不可抗力……我现在完全是靠“书”吃饭,有的时候,那种压力简直让人无法承受。说实在的,谁会不想踏实找个单位呢,我现在每个月得自己在手机上交社保,真挺麻烦又肉疼的。但是没有办法,有很多东西我也不愿意去写。 围绕个体展开的叙事,不一定就是个体叙事 新京报:对于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发展,你一直有着较为主动的关怀与思考。 袁凌:现在国内的非虚构写作,类型化越来越严重,或是和时代的整体焦虑贴得很近,或是掺杂了悬疑的角色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大量是类似于心理医生、急诊科大夫或者刑警,很多平台已经不太能接受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了。 在写作上,我一直有个立场,不写样本,不写典型,比如我写汉水,我就是要写它,写它的境遇和生命。中国现在大量的非虚构作品是在写样本,但这种问题是,你其实关心的并不是他们,只是说把他们作为一个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概念的论据。这些可以叫作非虚构写作,但不是非虚构文学的本质。 新京报:你提到了非虚构文学。在今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你就提出“非虚构文学”亟须面世,以区别于范围更广、且偏向于社会意义的“非虚构写作”。相比于后者,前者的边界更加明确,且意义主要收归文学本身,以写人为根本目的,并希冀以此为眼下非虚构“热热闹闹的僵局”破局。 然而,非虚构的文学性其实在今年上半年一度遭受过较大的质疑。今年3月云南空难的报道中,《MU5735航班上的人们》曾引发大量讨论,而焦点之一是公众对于作品中偏向文学性的描述部分看法不一。我明白你一直十分警惕与“热点”贴得太近,如今距离那场论争已经过去半年有余,也许是时候站在一段时间之外,重新回看当时的争议。你会怎么看那次讨论? 袁凌:哪怕是今天再去回看,我依然觉得那篇采访在操作上没有不当之处。我看了那篇报道,就是一些遇难者家属的回忆,只要没有编造,这里面没有任何伦理问题。遇难者家属中有些人想要宣泄,他们愿意接受采访;当然也会有人不愿意,拒绝就可以了,不能一概而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新闻报道还面临着内部也在不断消解彼此交往的空间。 非虚构写作在中国走到今天,概念仍然是相当模糊的。什么是非虚构写作?我们其实没有形成一套所谓的理论,在这个模糊的概念下写作,都只能靠题材出圈。所以我觉得,非虚构文学的提法是很迫切的,要承认它是文学,这个不是说文学的技巧,而是首先要承认它是人学,是以人的生命为对象的,不是以社会学理论为对象的。我想先尝试把这个独立性建立起来,不然永远都是题材先行,社会学分析加上文学修辞,千篇一律都是这样的东西。 电影《三峡好人》剧照。 新京报:你在此前的采访中也曾多次谈到,自己一直不喜欢宏大叙事,恰恰是那些被边缘化的能够保留一些个性和真实。近年来,公共空间涌现了很多关于个体的故事,像是前不久的“二舅”(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引发有关“消费苦难”“美化苦难”“升华平凡”的争议)……可围绕个体展开的叙事,就是个体叙事吗? 袁凌:这个不一定。首先,“二舅”的叙事中值得肯定的是,它确实让公众看到了“二舅”这个人的一生,但其中有很多处确实刻意在往公共情绪上靠。实际写作中会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故事的主人公的确就是一个新闻漩涡中的个体,写作者只是选了这个漩涡中的某一个人来写;还有一种是这个人其实不是漩涡中的人,他有他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但是写作者力图把它往漩涡上靠。 我一直不太喜欢后者那种写法,你写一个人,他身上像是折射出了一个时代,无论发生在他身上的什么事,都巴不得结合既有经验的理解框架去给出一个解释。这看上去好像很有社会意义,但我总觉得他人生中的每一程,每一个节点中会遇到的事,都像是排好了,是不是有点太精确了?他没有他的主动性吗?他被塑造成了一个时代的切片和样本,这本质上难道不是另一种宏大叙事的产物吗?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非虚构池子里,会大量是题材式的写作,它追求另外一种宏大,能带来流量。 新京报:之前提到,你觉得这两年自己越来越倾向于写边缘群体了,边缘群体难道不也是一种题材吗? 袁凌:边缘群体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现实,你也可以说它算是一种题材,但我不是把它当作题材来写,试图在一个人身上归纳出来这个群体的特征,我不是这么写。而且,它现在已经不是最热的时候了,比如当年“北漂”这些提法最热的时候,我是不愿意去写的,一写就会不自觉被卷入,当事人是在很极端的一种心理状态下,写作者也是如此,它都是速成下的一种宣泄,强化了一些的同时,也弱化了一些。现在“北漂”已经成了一种称呼,人们很自然就接受了,这时你再去写其中的个体的故事,才能还原为他(她)的故事。 电影《钢的琴》剧照。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在你看来,非虚构写作,或者广义而言的深度报道,如果未来要在国内往更深处走,最需要的是什么? 袁凌:如果先抛开压力不谈,那就是,独立意识。 采写/申璐 编辑/青青子 校对/卢茜小度的故事有哪些1
小度的故事有哪些2
小度的故事有哪些3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05日 星期日
版权保护: 【本文标题和链接】小度有多少故事(小度的故事有哪些) http://www.youmengdaxiazuofa.net/longxia8/72918.html

- 全部评论(0)